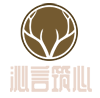非法集资类案件所引发的受害人民事诉讼问题简析
作者 金炳聪 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
前篇文章对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受害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是否属于民事受案范围等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但还未概括此类型的案件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本文作进一步分析,供大家探讨、交流:
一、受害人代位权诉讼中,受害人对被告人享有的债权是否属于“合法债权”。
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债权必须合法,这是必须达到的一个法律标准。对什么是“合法债权”,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9387号案件在事实认定部分认为:“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原告向中铁建业公司出借资金,因中铁建业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显然该债权系非法债权,原告无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另外也有一些同行与上述判决持一致的观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虽然这些债权系因他人非法吸存或集资诈骗所产生,但属单方非法行为所致,而非双方串通、共谋或明知违法而出借形成,债权人即是受害人,受害人享有要求返还被侵占财产的权利,国家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追缴、责令被告人退赔,这种债权依法应予以保护,正如笔者在前文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也支持了“受害人在司法机关已经依法追缴后仍无法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仍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这一观点。当然但在这类型案件中也会存在部分非法的债权利益,如一些犯罪分子以高息为饵吸引受害人资金,超出法律限定范围的利息属非法债权无疑,但对于未超过法律限定范围的利息是否属于非法债权存在争议,一部分观点认为,高息及合法利息均不应得到支持。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普通利息(在法律限定内的)应予以支持,高息不应支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此问题已经做出规定,《意见》第五项规定了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可见,按此文件之规定:无论是高息还是法律限度内的利息均认定为非法,应予以追缴,本金尚未归还的,应在本金中予以折抵。依此规定,法院在受害人代位权诉讼中也不应支持受害人请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但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向被告人所借资金是否应支付利息,已经支付的利息是否应在本金中予以折抵,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可参考案例,笔者认为次债务人应依其于被告的约定(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支付相应的利息,次债务人是资金的使用人,其是受益者,支付利息也完全合理、合法。而且在大部分集资类案件中,受害人一般无法得到完全清偿,清偿率甚至很少达到50%以上,大部分案件的清偿率低于10%,支持次债务人支付利息有利于最大限度内弥补受害人损失。
二、关于受害人行使代位权诉讼主体问题
被告所享有的这些债权利益属于全体受害人,单一受害人或部分受害人能否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实践也存在争议。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法院是支持单一或部分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当然也有部分法院要求全体受害人做为共同原告起诉,这种大而全的做法看似保障了全体受害人利益,但实践当中操作中难上加难。笔者接触这类型案件中受害人少者几十人多者三四百人,且分散全国各地,甚至远在国外,在此种情况下要求受害人全体起诉显然非易事。而且此类型案件基于维稳等因素需要,各地政府部门都会组织受害人成立债权人小组或选举债权人代表,但债权人小组或债权人代表在法律上并不能成为诉讼主体,即便是能成为诉讼主体,也因受害人过于分散且意见不一,导致相关事项无法及时表决,不利于维护广大债权人的根本利益。因此,支持单一或部分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于法不背,应予以支持。另,如果单一或部分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成功后,所得款项如何分配,如果次债务人向起诉的受害人直接清偿或法院直接得款后由诉讼的受害人直接领取该如何处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司法解释出台,可以在下次继续进行探讨。
三、 新类型网络P2P平台涉及非法集资类案件的维权思考
与传统的非法集资类案件不同,P2P“暴雷“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受害人,P2P受害人往往来自全国各地,单个平台所涉及受害人数比传统集资类犯罪更多,且受整个金融产环境影响,该行业大面积“暴雷”,极易导致受害人串联集体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也给公安机关办案带来了极大压力。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涉及刑事案件的P2P企业吸收存款的两大方式:一是制作假标,吸收受害人投资直接挪为自用,不存在次债务人;这种脱离了P2P本意,多涉及集资诈骗行为。二是具备正规标,将多个投资人的资金打散再集中打包将款顶出借给有需求的人,也就是我们所称的P2P借贷业务,由于在操作过程中进行保证还款承诺或其它违规行为导致被公安机关认定非法吸存。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由公安机关依法追赃并由法院判决退赔、追缴,是否能另行起诉取决于被告公司或实际控制人有无其它未执行或未被追缴的财产或债权。第二种情况借款人人数众多,通过公安机关的传统做法,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一旦借款人不予配合或无显性财产便很难继续追缴,因此,此类案件存在另行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受害人如何获取相关材料却也成为一个现实难题,因为每笔出借的资金属于共同出借人,如果获取这些共同出借人的信息进而达成共同诉讼维权的意思表示,也是难题,显然通过民事诉讼维权显然成本太大,且须耗费大量精力。在实践中,借贷平台或企业代投资人维权诉讼也较常见,在本次2018年P2P平台风波期间,个别法院对平台起诉次债务人或投资人起诉平台的诉讼案件采取了暂缓立案的做法,笔者对于这种做法不予置评。但考虑在“暴雷“之前平台将这类逾期还款的次债务人尽早起诉至法院,争取早日做出民事判决,那么即便是日后平台被认定涉嫌刑事违法,也可以直接由法院依判决生效的文书将次债务人列为被执行人,这样相比刑事立案后由公安机关追赃来得更为顺利一些。
四、针对次债务人强制执行法律制度的思考
正如非法集资案受害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实践中基本无法直接执行,基本依赖次债务人主动履行。但在德国民法典中,由于强制执行制度较为发达,破产程序十分完备,在债务人怠于使使其权利的情形下,可以依据强制执行制度申请法院就债务人的债权予以强制执行,从而可以起到与代位权行使相同的效果[1]。但就目前的环境与制度来看,我国均没有行使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不是完全空白,对于一些明确清晰的债权也是可以执行的,前提是被执行人无异议,这无异于次债务人主动履行。《执行规定》第61条至第69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相关制度。据这些条文规定,应符合三项要件:一是第三人向被执行人负有金钱债务。二是该债务已届履行期限。三是第三人对该债务并未提出异议。但现实生活中,即便是相关次债务人对债务进行了书面确认,其仍为提出一些诸如程序之类的异议,一旦提出异议,则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而且对这种异议也无法进行进一步审查,确定这种异议是否能合法成立。如果此种情况无法执行,法院又认为受害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则使受害人维权陷入了怪圈,明明被告人享有债权,法院即不执行也不审查判决,这种案例的增多,将极大损害司法公信力。
[1]王利明:《债权人代位权与撤销权同时行使之质疑》,《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