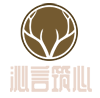非法集资类案件受害人维权之困境解析
(作者:金炳聪律师)
近年来非法集资类案件在全国各地频发,一方面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了刑事打击,净化投资风气,另一方面也维持了金融秩序与社会稳定。但被害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的损失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除司法机关依法依法追赃、追缴外,被害人也会采取后续措施,但往往举步维艰。下面本文就以笔者经办的案例为引,展开解析,供大家交流:
案例:2013年9月,戴某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11月25日被依法逮捕,后经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不服上诉于浙江省高院,高院维持原判,现戴某某在浙江某监狱服刑。刑事判决后,经过人民法院追缴,处理了戴某某名下的房产,一小部分戴某某民间借贷债务人(即次债务人)履行了部分债务,最终受害人清偿率仅为债权总额的8%。对戴某某享有的借贷债权未进行处理,这些债权金额达四千余万(涉及次债务人三十余人),且大部分经过次债务人二次确认,相关的借据、债务二次确认函原件均留存在当地金融办,法院执行机关仅对次债务人名下股权作了查封(基于现实情况,无法进行评估拍卖)。为此,戴某某债权人小组于2018年2月份开始委托律师分两批次对次债务人及债务保证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还款,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历经近一年多的审理,经多次开庭及补正材料,人民法院以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了案件的起诉。
案例引出的相关问题:
1、关于这类案件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问题。
被害人认为根据《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五条规定:“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受理。”因此对次债务人及保证人提出诉讼有法可依,而且法院无法对次债务人及保证人直接采取执行措施,在客观情况下也需要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确认相关的次债权。另外,债权人已经提供了次债务人向金融办出具的债务确认函,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证据也充分。
而次债务人及保证人则认为,债权人所提出的法释[2000]47号)第五条不能适用,已被新法所取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 229号)进一步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认为对被害人所提起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继续由司法机关进行追缴。
笔者认为,刑诉解释第139条及适用刑法64条之批复内容所针对的只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处理,已经确定被告人之刑事责任,依法追缴是司法机关的法律义务,如果还允许当事人另行起诉,会造成诉累,即便是案件受理判决,最终还是落到同一法院执行部门,因此确实有多此一举之嫌。但相关的最高院意见及案例中,对于经追缴未能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情况,又支持了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诉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1辑(2015年1月份)刊发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退赔不能弥补损失,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处理问题》一文中,最高院民一庭意见:“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应当予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案件中法院也认为:“在通过刑事追赃、退赔不能弥补被害人全部损失的情况下,赋予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相互补充的,并未加重被告人等人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并无不当”。因此,即便是仅关乎被告人名下财产的执行,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是会受理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并予以支持,更何况本案情况与此不同,本案中虽然被告与被害人的相关债权也已由司法机关通过刑事审判进行了确认,但被告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与保证人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部确认,以本案为例,金融办、法院执行部门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主张主要还是依赖于次债务人主动履行,金融办配合法院在联合追缴的过程中,也只是要求次债务人、保证人对债权进行确认,法院也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强制执行次债务人、保证人之财产。此种情况,应该允许被害人对这些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是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然在本案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受害人方均已向审理法院提交相关的实际案例并阐明了法院应予支持的理由,很遗憾法院还是直接驳回了被害人的起诉。
事实上,关于类似代位权诉讼案件在同一省不同区域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尽相同,如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该类型案件受害人提出代位权诉讼【(2015)浙金商终字第2334号】,法院认为:虽然(2013)金浦刑初字第17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各上诉人与第三人金某某之间的借贷均属金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各上诉人享有的对第三人金某某、李某某的债权系合法债权,符合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条件,各上诉人也系适格诉讼主体。故原审认定各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权不合法,驳回各上诉人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指定浦江县人民法院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被害人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此类诉讼非当不应轻易驳回,在审判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被害人之利益,此类案件的妥善处理非当有利于维护广大被害人权利,维持社会稳定,而且判决所作出的结果也直接可以由追缴部门作为执行依据,另外也可以借此打击因被告人判刑而逃避偿还义务的次债务人,可以说于各方均有利。
2、被害人向次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代位权时应注意的问题。
以本案为例,地方金融办在被告人戴某某被刑拘之后,便配合公安机关一起进行相关财产的追赃,相关的戴某某的对外债权信息全部由金融办进行登记,相关的债权凭证及次债务人对债务的重新确认函件均保管在金融办手中。但金融办最大的功能是维稳,至于如何追赃要依赖司法机关,又无法直接代表被害人进行诉讼维权,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极易导致相关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或保证期间,给后续民事诉讼带来极大的隐患,即便是被害人中间有懂法或有法律人士注意到了这一点,金融办、债权人小组等也会基于政府的要求进行统一步调的行动,这往往会忽略时效、期间的问题。金融办工作人员也会由于法律知识的局限及无诉讼经验而不会按法律之要求采取引发时效中断或其它补救之行动,从而导致后续诉讼之障碍。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已经在不同程度的出现,甚至诸如时效、期间的问题还会直接决定法院最后对案件的定性。被害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次债务人及保证人往往会以诉讼时效或保证期间以及不属于民事受害范围等要求驳回被害人的诉讼请求。如果法院依民事法律审查认为确实过了诉讼时效或保证期间,如基于这两点原因驳回被害人的诉讼请求,则次债务人、保证人便永远无需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显然不是法院及广大被害人所希望看到的,因而法院极可能会作出类似案件不属于受案范围的判决。但这样一来,法院如何直接对次债务人及保证人进行追缴似乎又限入了无法摆脱的法律困境。
因此,在非法集资类案件案发时,金融办应及时与律师进行法律层面对接,或尽快成立债权人小组,由债权人小组聘请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对这些次债务情况进行及时归类,并及时进行诉讼维权。
笔者也希望立法机关对次债务的追赃问题进行进一步细化,专门针对非法集资类案件诉讼维权出台相应司法解释,以维护广大被害人的权益,维持社会稳定。